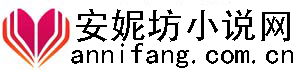60-70(22/28)
她原以为杨伯安与京都杨府决裂,当是与杨仲辅不和的,如今看来也不尽然。“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,这次你叔父出了不少力,你当亲去道声谢。”
起身往外走时,他似是想起什么,补充道:“建章也寻了好友帮忙,回程途中我们也当去致谢。”
“晓得了。”杨书玉眨巴着神采奕奕的双眸,乖顺地跟在杨伯安身后去见杨仲辅。
让人挑不错的礼节,较先前更为亲近的语气和态度,她在两位长辈那如春阳和煦般目光中,满怀真诚地给杨仲辅道谢。
在月渚没完成的认亲,好像得到了延续,杨仲辅忍不住笑着连连道好。许是日光晃眼,他眼角隐约可见细碎的光。
“书玉回车上稍候,爹爹有话同你叔父说。”
杨书玉点头应是,在转身时却见杨文先也不知何时凑到了谢建章身边,两人低声说着什么。
愉悦舒畅的心绪突然冷了下来,她踏凳上车时,鬼使神差地朝宫城的方向看了一会儿。
也不知道自己心中的失落从何而起。
“我意已决,为官非我所求,更何况如今朝局已然明朗,我留在京都无益。”
谢建章远远注视着杨书玉的一举一动,将她的小动作全盘看在眼里,答杨文先的话也一句不落,毫不敷衍。
“闻道犹迷,敢为文先,自家父为你起名时我就知道,这世道读书人的文心全然变了。”
“文人墨客读书不再为了增长学识,继往圣绝学,而为的是党争夺权,功名利禄,是以‘文先’都成了对晚辈的祝愿和期盼。”
“这不是家父想看到的文林,更与老太爷穷极一生掀起的文风相去甚远。”
“我自幼追随辅佐王爷,既是听从家父的遗愿,也是存了私心,想为谢府满门讨个公道。如今太后一党式微,我不想被京中风气同化,趁早抽身而退本就是上策,何来的可惜之说?”
他名满京都,是人人称道的谢郎君,从仕则前途无量,可这非他所求。
杨文先十分惋惜地顿足叹息,艰难开口问道:“那谢兄今后作何打算?”
“听闻田里的庄稼或果树若染了病害,庄户会立刻清除,待来年再栽种一批新苗。”
畅想今后要走的路,谢建章的语气跟着轻快起来,带着从容的笑:“既然现在的读书人过早沾染上官场习气,追捧钱权蔚然成风,那我便把老太爷的文心播撒在天真无邪的孩童心中。”
“林氏一族迁出京都后,林老太爷为传扬家学,曾在江陵设学。后林氏一族北迁,林老太爷便将自己生命余晖所建起的书院转托给伯父打理。”
“可惜伯父常年奔波劳碌,忙于商行事务,江陵书院虽有金银支撑,暂没有破灭的风险,可到底多年来没作出成绩,连中进士的学生也少。”
“谢某不才,虽未下场参加科考,却愿意去江陵书院寄余生。”
他抬手拍了拍杨文先的肩,语重心长道:“倒是你……”
继而他凑近杨文先,压低声音道:“等太后党落幕,无论结局是不是王爷交权,由皇上亲政,加设恩科已是板上钉钉,你还不抓紧温书,好来年下场一举夺魁?”
“谢兄……”杨文先连连摇头,无奈地笑出声来,“你惯会打趣我!”
他先前的惋惜和郁闷一扫而空,面上复呈现出鲜活少年的张扬来。
“以前我总以为林自初回京,他可以同你争高下。谁料他竟是北凉细作,没得叫人膈应!”
杨文先嫌弃而轻蔑地轻啧道:“叛国之徒,如何对得起清烈公?他甚至不配站在谢兄跟前!